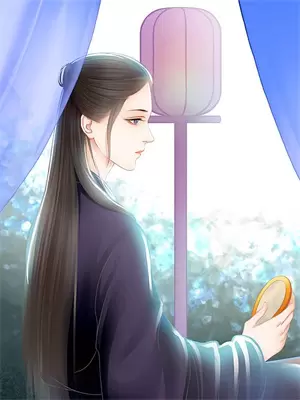注:故事中的人物名称属于虚构我们家乡有个流传已久的禁忌:深夜独自走在河边,
如果听到有人叫你全名,千万不要回头,也不要答应。老人们说,那是“水鬼”在找替身,
它们记不住活人的名字,只能笨拙地模仿着生前听过的呼唤。一旦你应了,
就等于和它签了契约,魂魄就会被它拖进冰冷的水底,成为它的替身,而它则能得以解脱。
我小时候有个最要好的伙伴,叫阿杰。我们俩天不怕地不怕,
对这些老一辈的迷信说法总是一笑置之,认为那不过是吓唬小孩的把戏。夏夜闷热,
我们常偷偷溜到村外的小河边游泳、抓萤火虫,对着空旷的河面大声怪叫,
嘲笑那些所谓的“水鬼”。那是一个异常闷热的夜晚,月光被薄云遮住,天地间一片朦胧。
我和阿杰又溜到了河边。河水黑沉沉的,缓缓流淌,只有偶尔泛起的微波反射着微弱的天光。
四周静得出奇,连往常聒噪的蛙鸣都消失了。不知为何,那天我心里有些莫名的不安。
阿杰却依旧兴致勃勃,他脱了上衣,朝着河水走去,嘴里还哼着不成调的歌。
我坐在岸边的石头上,看着他一步步走入齐腰深的河水。就在这时,一阵若有若无的声音,
贴着水面飘了过来。“阿杰……陈永杰……”那声音很怪,像是隔着水传来的,含糊不清,
带着一种湿漉漉的粘腻感。阿杰停下了动作,疑惑地转过头看我,
用眼神询问是不是我在叫他。我摇了摇头,心里猛地一紧,后背瞬间渗出了一层冷汗。
我张了张嘴,想提醒他那个禁忌,却因为紧张,一时没能发出声音。
“陈永杰……”呼唤声又响起了,这次清晰了一些,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急切和诱惑。
阿杰皱起眉,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——那片最深的、黑黢黢的河面,
下意识地应了一声:“谁啊?”就在他应声的刹那,
平静的河面突然毫无征兆地炸开一团水花!一只手,一只苍白浮肿、指缝间满是淤泥的手,
猛地从水下伸出,死死抓住了阿杰的脚踝!阿杰连一声惊叫都没能完全发出,
就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拽倒,“扑通”一声栽进了河里。我吓得魂飞魄散,猛地站起身,
只见阿杰在水中疯狂地扑腾,水花四溅,他的头几次冒出来,脸上满是极致的恐惧,他想喊,
却不断被拖入水下。我想跳下去救他,双腿却像灌了铅一样沉重,动弹不得。仅仅几秒钟,
河面就恢复了平静,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。只有那几个残存的气泡,
证明着刚才的恐怖并非幻觉。阿杰不见了。村里人闻讯赶来,打着火把,
用长竹竿在河里捞了整整一夜,一无所获。直到三天后,阿杰的尸体才在下游的浅滩被发现。
他的眼睛瞪得极大,几乎要凸出眼眶,脸上凝固着死前那一刻无法形容的惊骇。
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是,他的右脚踝上,清晰地印着五道乌黑发紫的指痕,
像是被什么东西紧紧攥过。从那以后,我再也不敢在夜晚靠近任何水域。甚至白天路过河边,
我都会快步离开。那个景象成了我永久的梦魇。许多年过去了,我离开家乡,在城市里生活,
试图用时间和距离淡忘那晚的恐怖。昨晚,我加班到深夜,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。
必须经过一条穿过城市公园的景观河。河两岸灯光昏暗,夜风习习,
吹得河水轻轻拍打着堤岸。四周寂静无人。就在我走到河中央的小桥时,一阵风过,
我似乎听到一个声音,一个贴着水面飘来的、含糊不清的声音,
带着记忆深处那种湿漉漉的粘腻感,它在呼唤我的名字,我的全名。我的血液瞬间冻结,
头皮一阵发麻。我不敢回头,死死咬住嘴唇,加快脚步,几乎是跑了起来。终于,
我冲回了家,反锁上门,背靠着门板大口喘气,心脏狂跳得像要挣脱胸腔。
应该……应该没事了吧?我没有回头,也没有答应。我不断安慰自己。
惊魂未定地走到洗手间,想用冷水洗把脸,让自己冷静下来。我拧开水龙头,
双手接住冰冷的水,拍在脸上。抬起头,看向镜子——镜子里,我的影像似乎有些模糊。
在我苍白的脸后面,在那本应是我身后浴室墙壁的背景里,
隐约映出了一片摇曳的、黑暗的水草,
以及一只……一只从黑暗中缓缓伸出的、苍白浮肿的手。我猛地闭上眼睛,
心里疯狂默念“是幻觉,都是幻觉”,冰凉的水珠还挂在我的睫毛和脸颊上,
带着刺骨的寒意。几秒钟后,我鼓足勇气,再次睁眼看向镜子——镜面光洁,
清晰地映出我身后狭小的浴室,瓷砖墙壁,挂着的毛巾,一切正常。我长长舒了一口气,
用力揉了揉脸,果然是太紧张,自己吓自己。然而,就在我准备转身离开时,
眼角的余光瞥见了洗手池。不锈钢水槽里,我刚才洗脸时溅出的水渍中,
似乎混着几丝极其细微、暗绿色的东西,像是腐烂的水草。我凑近了些,
一股若有若无的、河底淤泥般的腥味钻入鼻孔。我的胃一阵翻滚。那一夜我几乎没睡。
任何细微的声响都让我心惊肉跳。浴室的方向,我更是连看都不敢看一眼。天快亮时,
我才在极度的疲惫中迷迷糊糊睡去,却陷入纷乱的噩梦,
梦里尽是漆黑的水流、缠绕的水草和阿杰那张惊恐扭曲的脸。第二天是周末,
阳光透过窗帘照进来,驱散了些许夜晚的恐惧。我告诉自己必须振作,那一切都是心理作用。
我决定彻底打扫一下房间,尤其是浴室,或许能消除那种不安感。我走进浴室,拧开水龙头,
想用大量流动的水冲洗掉昨晚的痕迹。水流很正常,清澈透明。我稍微安心,
开始清理洗手池。可当我伸手去拔池底的塞子时,指尖触到了一种异样的、滑腻的阻碍感。
我捏住那东西,把它拽了出来——那是一小绺纠缠在一起的、湿漉漉的黑色长发,
绝不是我的。恐慌再次攫住了我。我强忍着恶心,把那绺头发扔进马桶冲掉。
看着水流漩涡将它卷走,我靠在墙上,心跳如鼓。这房子是我独居,最近根本没有女性来访。
这头发是哪里来的?接下来的几天,这种细微的、令人不安的迹象越来越多。晚上,
我总听到从浴室方向传来极轻微的、像是水滴落在水面上的声音,嘀嗒,嘀嗒,
但我去检查时,所有水龙头都关得紧紧的。空气中那股若有若无的淤泥腥气,
也始终挥之不去,尤其是在浴室里。更让我毛骨悚然的是,
我发现自己开始对一些常去的、靠近水源的地方产生莫名的恐惧。路过公司的景观喷泉,
我会绕道而行;看到小区中央的锦鲤池,我会感到呼吸困难。仿佛有一种无形的力量,
正在将我拉向某个水域。昨晚,我实在无法忍受浴室里那股越来越浓的腥味,
决定彻底清洁浴缸。当我放水冲刷浴缸内壁时,清澈的水流中,突然冒出了几个细小的气泡,
接着,一小片惨白的、像是被水泡了很久的碎布片,从排水孔里被水流带了上来,
粘在了浴缸壁上。那布料的颜色和质感,让我瞬间想起了多年前,阿杰被捞上来时,
身上那件被水泡得发白的衬衫。我再也无法欺骗自己了。它不是幻觉,它跟着我回来了。
从家乡那条黑沉沉的河,跟着我来到了这座城市,进入了我的家。
它没有因为我的不应答而放弃,它用了更迂回、更缓慢的方式,
正在一点点地渗透进我的生活,我的空间。此刻,我坐在客厅里,不敢靠近浴室一步。
屋子里很安静,只有我粗重的呼吸声。但我能感觉到,它在那里。在镜子的后面,
在排水管的深处,在每一滴即将滴落的水珠里。它在等待。我不知道它在等什么,
也不知道下一次,它会以什么样的方式,出现在我眼前。或许,它只是在等我崩溃,
等我主动走向那片它所在的、冰冷的水域。夜,还很长。我尝试联系老家的亲戚,
拐弯抹角地问起那条河和当年的事。电话那头,
堂叔的声音带着睡意和不耐烦:“多少年的事了,谁还记得清?那河早几年就干了,
现在修成广场了。”河干了?不知为何,这消息并没让我感到丝毫轻松,
反而觉得那东西失去了最后的束缚,更像一缕无所依凭的幽魂,彻底黏上了我。
我开始避免使用家里的水。刷牙用瓶装水,洗脸用湿毛巾擦,甚至不敢用马桶冲水,
生怕那漩涡会带出更可怕的东西。家里弥漫着一股不洁的气息,
而我像一只被困在干燥陆地上的鱼,焦渴又恐惧。晚上,我枕着胳膊浅眠,
任何细微的水声都会让我惊醒。我听到过浴室水龙头自己拧开的“嘎吱”声,
也听到过马桶水箱无声注满又悄然排空的循环。精神濒临崩溃的边缘,
我翻出奶奶当年悄悄塞给我的一张叠成三角形的黄符,据说能辟邪。我把它紧紧攥在手心,
似乎能感到一丝微弱的热度。我鼓起勇气,拿着符纸走向浴室,想将它贴在镜子上。
就在我伸手的瞬间,镜面突然蒙上了一层浓重的水汽,水珠蜿蜒滑下,像是无声的泪水。
符纸在我手中迅速变得潮湿、冰冷,那股微弱的热感消失了。最恐怖的事情发生在一个凌晨。
我被喉咙里火烧火燎的干渴逼醒,迷迷糊糊走到客厅想拿水,
却鬼使神差地拧开了厨房的水龙头。水流哗哗作响,在寂静中格外刺耳。我俯身想去接水,
却看到流出的根本不是透明的水,而是浑浊的、带着泥沙的暗黄色液体,
散发着我熟悉又作呕的河底腥气。我猛地关掉龙头,干呕起来。我意识到,它在戏弄我,
也在消耗我。它用这种无处不在的细微侵蚀,提醒我它的存在,放大我的恐惧。
它并不急于一下子夺取我的性命,而是要让我在这日复一日的折磨中,自己走向崩溃。
我甚至开始出现幻觉,看到地板上偶尔会出现湿脚印,从浴室门口延伸出来,走几步又消失。
昨晚,我坐在漆黑的客厅里,放弃了抵抗般的听着从浴室方向传来的、持续不断的滴水声。
我知道那不是漏水。那声音很有规律,嘀嗒……嘀嗒……像是在倒数。然后,
我听到了另一个声音,混合在滴水声里,极其微弱,像是隔着很厚的水层传来的呼唤,
不再是叫我的名字,而是反复念叨着两个字:“……替身……替身……”天快亮了,
阳光却无法再带来任何安慰。我知道它就在这里,在这个房间里,在我每一次呼吸的空气里,
在我对水源的本能渴望里。它在耐心等待,等待我精神防线彻底垮掉的那一刻,
等待我主动走向它,完成那个多年前被阿杰应下的、未尽的“契约”。
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。或许下一次口渴难耐时,我会自己走向水龙头,
喝下那浑浊的流水。或许,就在今晚。我尝试联系懂行的老人。辗转多人,
终于找到一位据说能处理这种事的神婆,住在邻市。我在电话里语无伦次地描述,
她沉默地听着,最后只沙哑地说了一句:“它缠上你不是因为你应了,是因为你‘看见’了。
看见,就是一种连接。带上它第一次找上你时身边的东西,明天午时过来。”电话挂断,
我愣在原地。“看见”……是啊,我看见了阿杰被拖下水,看见了那水下的手,
看见了这么多年它留下的种种痕迹。翻箱倒柜,
我终于找到了那个夏夜穿的衣服——一件早已褪色的旧T恤。它被压在箱底,
泛着一股陈旧的、难以言喻的气味,并非霉味,而是一种……淡淡的河腥气。
我把它塞进一个塑料袋,像是抓住最后一根稻草。这一夜,滴水声前所未有地密集,
像是在催促,又像是在愤怒地阻止。第二天中午,我准时到达神婆的住处。
那是一个光线昏暗的老公寓,空气中弥漫着香火和草药混合的奇异味道。
神婆是个干瘦的老太太,眼神却异常锐利。她让我拿出那件T恤,只是瞥了一眼,
眉头就紧紧皱起。“怨气深重,而且……不止一个。”她点燃三炷香,烟雾笔直上升,
却在快到天花板时突然扭曲、散开,像是被无形的东西搅乱。神婆画了一张符,
让我用矿泉水混合符灰喝下。那水带着灰烬的苦涩,滑过喉咙时,
我竟感到一丝短暂的、奇异的清明,仿佛一直萦绕在耳边的水声和低语都远去了。
她将另一张折好的符塞进我手里:“拿好,贴身放着。回去的路上,无论听到什么,
看到什么,别回头,别应声,直接回家。把这张符贴在你家水源总闸上。记住,
太阳落山前必须贴上。”回程的路上,我紧紧攥着口袋里的符,手心全是汗。起初一切正常,
车载广播播放着轻快的音乐。但当我驶上通往家方向的那条僻静公路时,
广播信号开始断断续续,夹杂着刺耳的杂音,杂音里,
似乎有模糊的、很多个声音重叠在一起的哭泣和呼唤。我猛地关掉广播,心跳如擂鼓。
透过后视镜,我看到后座车窗上,不知何时蒙上了一层水汽,正缓缓汇聚成一道道水痕。
我不敢细看,猛踩油门。车子却突然变得沉重,像是载满了湿透的泥沙,
引擎发出吃力的轰鸣。更可怕的是,我感觉有一股冰冷的、湿漉漉的气息,
正从空调出风口缓缓吹出来,带着浓烈的河底淤泥味。我死死握住方向盘,指甲掐进掌心,
牢记着神婆的叮嘱:别回头,别应声。终于看到了小区的大门。我几乎是冲出车子,
狂奔上楼。冲进家门,我一眼就看到客厅的挂钟——离太阳落山只剩下不到半小时。
我掏出符纸,冲向厨房角落里的水表箱,手抖得几乎握不住那张薄薄的黄纸。
就在我撕开胶带,准备将符纸贴上去的瞬间——厨房和浴室的所有水龙头,
同时猛地自动拧开到了最大!“哗——!”巨大的水流声如同瀑布般冲击着我的耳膜,
浑浊的、带着泥沙的黄褐色水柱喷涌而出,迅速漫过水池,流到地板上。那水中,
似乎有无数黑色的发丝在翻滚、蠕动。我僵在原地,
眼睁睁看着手中的符纸被空气中骤然加剧的、湿冷的风吹得剧烈抖动,几乎要脱手而去。
挂钟的指针,无情地指向日落时分。屋内,水还在疯狂地涌出,仿佛要将整个空间淹没。符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