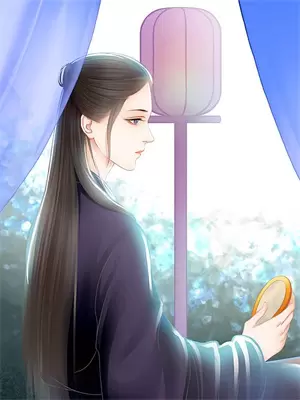妈的头七,晚上九点整,家族群里安静得像个坟场。我哥陈峰,突然扔出两个字。“快逃。
”然后,是一张图片。那是一张自拍遗照。照片里,他坐在自家客厅的沙发上,脸色惨白,
对着镜头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。他手里攥着一把黑色的桃木梳。我认得,
那是我妈最喜欢的一把,陪了她二十多年,梳齿都磨圆了。1. 梳子索命一小时后,
电话打到我爸手机上。我哥死了。用我妈那把梳子,从喉咙捅了进去,贯穿了。
警察说是自杀。没人信,一把梳子怎么可能捅穿喉咙?但法医报告就这么写的。
全家人都乱了套,哭喊声,咒骂声,电话铃声,混在一起,要把房顶掀了。只有我没动。
我坐在自己房间的床上,盯着手机屏幕,全身的血都像冻住了。我把那张遗照,一点点放大,
再放大。照片的背景,是我哥客厅里的一面穿衣镜。镜子很干净,映出了他家的摆设,
还有……他身后站着的一个人影。一个穿着我妈下葬时那件寿衣的女人。她正对着镜子,
也就是对着拍照的我哥,微笑。不,她不是在对我哥笑。她的脸微微侧着,目光穿透了镜子,
穿透了手机屏幕,直勾勾地看着我。她也在对我笑。我猛地把手机扔了出去,手机砸在墙上,
屏幕碎裂,黑了下去。可那个笑容,像用烙铁烫在我的视网膜上,怎么也甩不掉。
我听见自己牙齿打战的声音,咯咯作响。我慢慢扭动僵硬的脖子,
看向我房间里那面立在衣柜旁的镜子。镜子里,我的身后,空无一人。我松了口气,
可下一秒,心脏就停跳了。镜子里的我,嘴角正不受控制地,一点点往上翘。
翘成一个我妈生前最常有的,那种温柔又诡异的弧度。2. 镜中诡笑“操!”我吼了一声,
一拳砸在镜子上。镜子里的那个“我”瞬间消失,
取而代之的是蛛网般的裂纹和我指关节上渗出的血。剧痛让我清醒了一点。我冲出房间,
客厅里乱成一锅粥。我爸坐在沙发上,像一滩烂泥,我二叔在旁边拍着他的背,
嘴里骂骂咧咧,不知道在骂谁。“陈野!你他妈跑哪去了!你哥出事了你还躲在屋里!
”二叔看见我,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。我没理他,径直走到我爸面前。“爸,哥的手机呢?
他发在群里的那张照片……”我爸猛地抬起头,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瞪着我,
他的嘴唇哆嗦着,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二叔一把推开我,“你哥都死了!
你还惦记他那破手机干什么!滚一边去,别给你爸添乱!”“那张照片有问题!”我冲他吼,
“我哥不是自杀!”“不是自杀是啥?他妈的被鬼杀了?”二叔啐了一口,
“我看你跟你哥一样,都疯了!你妈一走,你们俩魂也跟着走了!”他的话像一盆冰水,
把我从头浇到脚。我哥疯了?对,在妈出事之后,我哥就不太正常。妈是突发心梗走的,
走得很突然。葬礼上,我哥一滴眼泪都没掉,只是死死盯着我妈的遗像,眼神很奇怪。
后来几天,他把自己关在家里,谁也不见。我给他打电话,他总说些胡话。他说,妈回来了。
他说,妈不是来跟我们团聚的,是来收账的。我当时以为他悲伤过度,脑子不清醒,
还劝他去看医生。现在想来,他说的每一句话,都像是一句句的遗言。“收账……收什么账?
”我喃喃自语。“收你们的命!”一个声音突然在我脑子里炸开,是我妈的声音。那么清晰,
那么真实,就像她正贴着我的耳朵说话。我浑身一激灵,环顾四周。
客厅里的人都在忙着打电话,或者相互安慰,没人注意到我的异常。幻觉,一定是幻觉。
我用力掐着自己的大腿,试图用疼痛驱散脑子里的声音。可那声音还在继续。“你哥的账,
收完了。现在,轮到你了,我的好儿子。”我再也站不住了,扶着墙冲进卫生间,
打开水龙头,把冷水往脸上猛泼。我抬起头,看着镜子。镜子里的我,脸色惨白,
头发湿漉漉地贴在额头上。一切正常。我稍微松了口气,准备出去。手刚碰到门把手,
卫生间的灯,闪了一下。灭了。整个空间瞬间陷入一片死寂的黑暗。我摸索着墙壁,
想去开门,可那个门把手,怎么也拧不动,像是从外面被锁死了。“谁?谁在外面?”我喊。
没人回答。只有水龙头里,滴答,滴答的水声。不对。那不是水声。
那是……梳子轻轻敲击瓷砖的声音。一下,又一下。笃。笃。笃。声音,就在我身后。
3. 梳子诅咒我全身的毛都炸起来了。我能感觉到,有个东西在我背后,很近,
近到我能闻到一股熟悉的、腐朽的木头味。是我妈那把桃木梳的味道。我不敢回头。
我僵在原地,连呼吸都忘了。“陈野。”我妈的声音,这次不是在脑子里,
而是真的在我耳边响起。冰冷,没有一丝感情。“转过来,让妈妈看看你。”我死死咬着牙,
用尽全身的力气,吼了一句:“滚!”身后的声音消失了。卫生间的灯,啪的一声,又亮了。
我猛地回头,身后空空如也。门把手“咔哒”一声,松了。我连滚带爬地冲了出去。
客厅里的人都用一种看神经病的眼神看着我。“陈野,你鬼叫什么!”二叔一脸不耐烦。
我爸也皱着眉,“大呼小叫的,像什么样子!”我看着他们,张了张嘴,却什么都说不出来。
我说我妈回来了?说她就在这个家里?说她下一个要杀的就是我?他们只会觉得我疯了。
就像他们觉得我哥疯了一样。不行,我不能坐以待毙。我哥说“快逃”,一定有他的道理。
这个家,不能待了。我找了个借口,说要去我哥家看看,有没有什么遗物需要整理。
我爸挥了挥手,让我快滚。他看我的眼神,很复杂,有厌烦,有悲伤,
还有一丝……我看不懂的恐惧。我抓起外套和车钥匙就往外跑,一刻也不敢多留。
我哥的公寓在城西,开车过去要半个多小时。一路上,我把车里的音乐开到最大,
试图用噪音压过心里的恐惧。公寓楼下已经拉起了警戒线,有两个警察守着。
我说是死者的弟弟,想进去收拾东西。警察不让,说案发现场不能随便进。
我塞了两包烟过去,好说歹说,才通融了一下,让我进去十分钟,而且不能乱动东西。
我哥的家,不大,一室一厅,收拾得很干净。除了客厅地毯上那块已经变成暗褐色的血迹。
我强忍着胃里的翻江倒海,快速扫视着房间。我哥是个很细心的人,
如果他想给我留下什么线索,一定不会放在很明显的地方。我拉开他书桌的抽屉,翻了翻。
除了些账单和文件,没什么特别的。我又去翻他的床头柜。柜子上放着一本书,
是本很旧的《山海经》,书页都泛黄了。我记得,这是我哥从小就喜欢看的书。
我随手翻了翻,一张书签从里面掉了出来。书签是片枫叶,已经干枯了。
上面用黑色的水笔写了两个字。“老宅”。我心里一动。老宅,是我们家在乡下的祖屋。
我爷爷奶奶去世后,那里就一直空着,十几年没人住了。我哥让我去老宅?就在这时,
我眼角的余光瞥见书桌底下,好像有个东西。我蹲下去,伸手一摸,是一个小小的录音笔。
我心里一阵狂喜,立刻按下了播放键。录音笔里,先是一阵嘈杂的电流声。然后,
我听到了我哥压抑着恐惧的、急促的呼吸声。
子……就站在门口……”“爸骗了我……他什么都知道……他骗了我们所有人……”“陈野,
快逃……别回家……去老宅……井……”录音到这里,戛然而止。最后那个“井”字,
他说得含糊不清,像是被人掐住了脖子。我把录音笔紧紧攥在手里,冷汗顺着额头流了下来。
爸骗了我们?老宅……井?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?我必须马上去老宅。
4. 老宅秘密我从我哥家出来,天已经黑透了。我没有回家,直接开车上了去乡下的高速。
老宅在一百多公里外的一个小山村里,路不好走,估计要开两个多小时。
我爸的电话一个接一个地打过来,我一个都没接。我现在谁也不信。我哥的遗言像一根刺,
扎在我心里。“爸骗了我……他什么都知道……”他到底知道什么?我妈的死,我哥的死,
难道都和他有关?我越想越心寒。车开到一半,下起了雨。
雨刮器在挡风玻璃上疯狂地来回摆动,还是看不清前面的路。车里的收音机,
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打开了。里面没有音乐,也没有新闻,只有一阵阵的“沙沙”声。
在“沙沙”声的间隙,我好像听到了一个女人在哼歌。那是我妈最喜欢的一首老歌。
我猛地伸手去关收音机,可那个按钮就像失灵了一样,怎么按都没反应。
女人的哼唱声越来越清晰,越来越近。就在我旁边的副驾驶座上。我头皮发麻,不敢转头。
我只能死死盯着前方被雨水模糊的路,把油门踩到底。车速已经到了一百四,车身开始发飘。
“开慢点,儿子。”我妈的声音幽幽地响起,“路滑,不安全。”我他妈快疯了。
我一拳砸在收音机上,那玩意儿总算安静了。副驾驶的哼唱声也停了。
我透过后视镜往后看了一眼。后座上,空荡荡的。可我总觉得,有什么东西,正坐在那里,
透过镜子,冷冷地看着我。我再也不敢看后视镜了,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开车上。
两个多小时的路,我感觉像开了一个世纪那么长。终于,在凌晨一点多,
我看到了村口那棵大槐树。老宅到了。村里一片漆黑,家家户户都睡了。我把车停在村口,
没敢开进去。老宅在村子最里面,靠着山脚,是个独立的院子。院门上的铁锁已经锈死了,
我找了块砖头,砸了半天才砸开。院子里杂草丛生,比我都高。正屋的门虚掩着,我推开,
一股发霉的味道扑面而来。我打开手机的手电筒,照了进去。屋里积了厚厚的一层灰,
桌椅板凳都蒙着白布,像一个个披着孝服的人。我哥说,线索在老宅的井里。我记得,
院子角落里确实有口老井,我小时候还差点掉进去过。我穿过齐腰深的杂草,找到了那口井。
井口被一块巨大的石板盖着,上面长满了青苔。我一个人根本搬不动。
我找了根手臂粗的木棍,插进石板的缝隙里,用尽全力去撬。石板纹丝不动。
我急得满头大汗,对着石板又踹又踢。就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,我脚下的地,好像动了一下。
不是错觉。我低头,用手电筒一照,发现井边有一块地砖是松动的。我把地砖抠开,
下面是一个小小的、上了锁的铁盒子。锁已经锈得不成样子,我用砖头几下就砸开了。
盒子里,没有金银财宝,只有一本用油纸包着的老旧日记本。还有一把小一点的,
看起来更古老的桃木梳。和害死我哥那把我妈的梳子,几乎一模一样。
5. 换命梳日记本的封皮已经烂了,字迹也因为受潮而变得模糊。我翻开第一页,
上面的字迹,我认得。是我奶奶的。日期是四十年前。“六月十五,晴。今天,
我去见了山里的那位‘先生’。为了给陈家求一个根,我什么都愿意做。”“六月十八,雨。
‘先生’给了我一把梳子。他说,这是‘换命梳’。用它梳头,能换来子孙满堂。但这是借,
有借,就得有还。”“六月二十,晴。我用了梳子。晚上,我丈夫回来了。他很高兴。
”我往后快速翻着。日记的内容很琐碎,都是些柴米油盐的家常。直到一年后。“七月初一,
阴。我生了,是个儿子。家里人都很高兴。只有我知道,代价是什么。”“‘先生’说过,
从我儿子这一代开始,陈家的长子或长女,活不过他们的母亲。母亲头七之日,
就是‘梳子’来收账之时。除非,能找到下一个‘接梳人’。”我脑子“嗡”的一声。我爸,
就是我奶奶唯一的儿子。他是陈家的长子。我奶奶……是怎么死的?我记不清了,
我那时候还很小。我只记得,奶奶死后,爷爷很快也跟着去了。家里人说,爷爷是思念过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