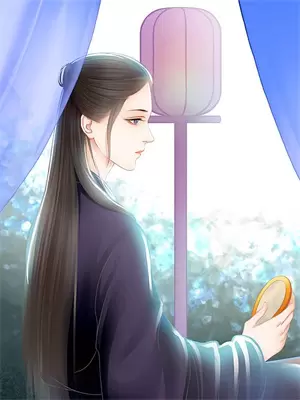一九九零年,夏,渝都。暑气像是浸透了油的棉絮,
厚重粘腻地包裹着这座山城的每一个角落。长江与嘉陵江的水汽在白日里被烈日蒸腾,
傍晚又随着山风卷回来,让空气里始终弥漫着一股挥之不去的潮湿。白日里,
蝉鸣嘶哑得像是被晒焦的棉线,从老黄桷树的枝叶间钻出来,搅得人心烦意乱。到了夜晚,
微风也带不来多少凉意,反而吹动老旧的窗棂,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,
那声响不像是木头摩擦,倒像是有人隔着玻璃,用指甲轻轻刮挠,
又像是某种不怀好意的窃窃私语,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。故事,
就发生在南区一片密集的居住区里,这片房子紧挨着一家规模不小的国营纺织厂,
是典型的厂区家属院。两栋七层高的筒子楼,像两个沉默而疲惫的巨人并肩矗立着。
楼体是陈旧的水刷石墙面,当年建厂时图省事,水泥里掺的沙子不够细,
经年累月的风雨冲刷和纺织厂烟囱里飘出的煤灰侵蚀,
在墙面上留下了大片深褐色的污渍和斑驳的痕迹,如同老人脸上纵横交错的寿斑。没有电梯,
狭窄陡峭的楼梯隐藏在幽暗的楼道深处,
每一级台阶都被无数双脚打磨得中间凹陷、边缘粗糙,积着厚厚的灰尘,
偶尔有孩子掉落的糖纸或大人丢弃的烟蒂嵌在缝隙里,成了岁月的印记。楼梯转角的平台上,
总是堆着各家舍不得扔的旧家具,掉漆的木箱、断了腿的板凳、蒙着塑料布的旧自行车,
在昏暗里像一个个沉默的影子。两栋楼之间,有一块不算宽敞的水泥坝子,
约莫半个篮球场大小,这是孩子们白天追逐打闹的唯一场所。坝子边缘几棵歪歪扭扭的老树,
夏天开着紫白色的花,落得满地都是,踩上去黏糊糊的。但一到晚上,这片坝子就格外寂静,
仿佛白日的喧闹被什么东西一口吞了,天色擦黑开始就进入了静态。没有孩子哭闹,
没有大人闲聊,连狗都不怎么叫,只有老树的叶子在风里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,
听着像极了有人在叹气。坝子的正前方,孤零零立着一个莫名其妙的高台,高出地面约一米,
方方正正,用青灰色的砖块砌成,表面坑坑洼洼,像是某种废弃的基座。
没人知道这高台是干什么的,老工人说建厂时就有,年轻点的猜是以前放机器的台子,
孩子们则喜欢爬上去玩耍,直到有一次一个小孩从上面摔下来磕破了头,
厂里才用铁丝网围了半圈,可依旧挡不住胆大的孩子翻墙上去。高台之后,
便是一堵极高极长的砖墙,足有两米多高,灰扑扑的墙头拉着锈迹斑斑的铁丝网,
网眼上挂着干枯的藤蔓和塑料袋,在风里飘来荡去。这堵墙像是一道无形的界限,
将这两栋楼、这块坝子,严严实实地与外界隔离开来。
墙的另一边是一条同样外面马路的小道,而墙内,就是自成一派的压抑小天地。老住户们,
尤其是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,茶余饭后总爱搬个小马扎坐在坝子角落,摇着蒲扇念叨些旧事。
他们说,早在这两栋楼还没影儿的时候,
这块地皮上原本是一座香火不算鼎盛但也不曾断绝的小庙,可老人们又说里面供的不是菩萨,
是个黑面娘娘,穿着红衣裳,手里捏着一串佛珠,脸是黑的,眼睛却亮得吓人。
住在一楼的张婆婆牙快掉光了,说话漏风,她含含糊糊道:“逢年过节的,
我们就去给黑面娘娘烧炷香,有位师太也和善,还给我们这些娃娃发糖吃。
”一九七零年厂里要扩建宿舍,推土机毫不留情地就把那庙给强拆了。老人们说,拆庙那天,
天阴得像要塌下来,师太跪在庵门口哭,说这地方镇不住了,可没人听她的。
那时候破四旧的余威还在,大家都觉得这些是封建迷信。推土机一铲子下去,就把木梁掀了,
神像被推倒在地,脑袋滚到了墙角,脸上的黑漆掉了一块,露出里面的木头本色看着像在哭。
更有一种隐秘的传言,是老人们压低声音说的,说这地方自古以来就阴气重,不太平,
长江涨水的时候,这儿以前是片乱葬岗,淹死的、饿死的,都往这儿扔。那座庙的存在,
就是为了镇住地下的脏东西,黑面娘娘就是镇物。如今庙没了神像毁了,封印自然解除,
那些被镇压了不知多少年月的邪祟,也就慢慢地溜达出来了。当然,这种怪力乱神的说法,
在讲究科学的年代,大多只限于老人之间私下流传,年轻人更是嗤之以鼻。王刚,
就是不信邪的年轻人中的一个。今年二十九,差一岁就满三十,个子不高,皮肤黝黑,
肩膀宽宽的,一看就是干活的好手。二十岁那年,他顶替父亲进了纺织厂,一干就是快十年。
厂里的工作是三班倒,早中夜轮流转,他在细纱车间,
每天面对的是轰鸣的机器、漫天飞舞的棉絮粉尘,还有永远也做不完的活儿,
把棉纱绕成锭子,再送到下一道工序,一天下来,鼻孔里、耳朵里全是白花花的棉絮,
连咳出的痰都是带棉丝的。辛苦自不必说,但王刚性子憨实,肯吃苦,话不多,手脚却麻利。
他家里条件不好,父母在乡下种地,还有个弟弟在读书,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多攒些钱,
在渝都站稳脚跟,早日娶上个媳妇,成个家,把父母接到城里来。为了这个目标,
他常常主动帮那些有家事拖累的工友顶班,尤其是别人都不太愿意上的深夜班,
深夜班补贴多,一个月能多赚十块钱,对他来说,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。长此以往,
他的睡眠严重不足,眼袋深重得像挂了两个小口袋,脸色总是带着一种缺乏日照的苍白,
嘴唇也常常干裂。但每次发工资,他把钱分成三份,一份寄给家里,一份存起来,
一份留作生活费,看着存折上缓慢增长的数字,想到未来那个模糊却温暖的家,
他就觉得一切都值。前不久,厂里终于给他分了房,就是这两栋筒子楼其中一栋的五楼,
一个单间。虽然只有十几个平方,墙壁上还留着前一任住户贴的旧年画,
墙角有一块发黑的霉斑,而且要和隔壁的老王家共用厨房厕所,但王刚已经心满意足了。
他花了半个月工资买了新的床单被套,又从旧货市场淘了个木衣柜,把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,
晚上躺在床上,听着窗外的蝉鸣,都觉得是乐声。“什么阴气重,什么邪祟作怪?
”他常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念叨。“我王刚行得正坐得直,浑身阳气足,怕个球!”这天夜里,
又是他上深夜班。子夜零点接班,他得像往常一样,在十一点左右出门。夏夜闷热,
狭小的房间更是如同蒸笼,水泥地面被晒了一天,散发出阵阵热气,连空气都像是烫的。
王刚用搪瓷盆接了点凉水,胡乱抹了把脸,水珠顺着脸颊往下淌,落在锁骨上,
带来一丝短暂的清凉。他套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作服,领口磨得发亮,
袖口还缝了一块补丁,那是他母亲去年来的时候给补的。
拿起放在床头的手电筒和饭盒准备出门。望了望窗外,夜色已经浓得化不开,
月亮躲在云层后面,只透出一点朦胧的光。他下意识地朝对面那栋楼扫了一眼,
动作猛地顿住了。对面七楼,最靠边的那户人家。黑漆漆的阳台里,
似乎……挂着个什么东西。那东西长长的,直溜溜地垂着,上端隐没在阳台顶部的阴影里,
下端离地大概一尺来高,一动不动地悬在那里。借着云层缝隙漏出的一点月光,
能看出一个模糊的、人形的轮廓头是圆的,身体是直的,胳膊垂在两边,
像一个……吊着的人。王刚心里猛地一怔,心脏咚咚地跳了起来。他的视力极好,
这是当年差点被选去当兵时测出来的,在昏暗里也比常人看得清楚。他揉了揉眼睛,
再仔细看…没错,那轮廓,那垂坠感,太像一个人了。那是谁家?他眯着眼,
努力在黑暗中辨认。对面七楼的住户最靠边的那间,对了,是厂里那对年轻夫妇,
男的叫李建军,三十出头,在机修班当钳工,人长得高高瘦瘦,说话总是带着笑。
女的名叫张小兰,比李建军小两岁,也在细纱车间,和王刚是一个车间的,
只是不在一个班组。他们结婚刚满一年,厂里照顾新婚夫妇,特意分了这七楼带阳台的单间。
要知道,带阳台的房子可是抢手货。平时上下班碰到,张小兰会笑着喊他刚子哥,
李建军也会递根烟给他,关系不算亲近,但也算熟络。一股寒意瞬间从尾椎骨窜上头顶,
让他激灵灵打了个冷颤。三伏天里,这股寒意却冷得他牙齿都差点打颤。
他下意识地抬手摸了摸后颈,全是冷汗。“出事了?”他第一反应是赶紧过去看看,
抬腿就要往门口走,但刚走两步,又猛地停住了,抬腕看了看那块老旧的上海牌手表,
表盘上的荧光指针已经指向十一点过五分。深夜班是零点准时接班,从住的地方到车间,
走路要十五分钟,要是现在过去敲门,万一真是误会,耽误了时间,上班迟到是要扣钱的。
迟到十分钟以上,当天的工资就没了,更别说这个月的全勤奖。“或许是自己眼花了?
夜里光线不好,看错了也是常有事。也许是谁家晾的衣服没收,风一吹,形状看着像人?
”最终,纠纠结结,对迟到扣钱的担忧,还是暂时压过了那瞬间的不安。他深吸一口气,
暗骂自己疑神疑鬼,不就是个影子吗?有什么好怕的!他用力带上门,哐当一声,
在寂静的楼道里显得格外响亮,他甚至听到对面邻居家传来一声咳嗽,
大概是被他的关门声吵醒了。噔噔噔,他快步下楼,楼梯间的黑暗里,他的脚步声像是敲鼓,
回荡在狭窄的空间里。然而,越是往下走,脑海里那个悬挂着的影子就越是清晰。
那绝对不是衣服!衣服不会有那种僵直又微微晃动的姿态,不会有那种脑袋耷拉着的角度。
纺织厂的工作服都是浅色居多,职工家里的衣服也大多是蓝、灰、白,那影子却是深色的,
在月光下呈现出一种晦暗的、像墨汁一样的质感,连月光都透不过去。
“万一……万一是真的呢?”一个可怕的念头冒了出来,“万一张小兰真的出事了,
我这一走,耽误了救人……”这个念头一旦升起,就像藤蔓一样紧紧缠绕住他的心脏,
勒得他喘不过气。走到三楼的时候,他脚步放慢了,心里的愧疚感越来越重。他停下脚步,
靠在冰冷的墙壁上,胸口起伏着,汗水顺着额头往下淌,浸湿了工作服的领口。“不行,
得去看看!”他咬了咬牙,就算迟到扣钱,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可能发生的悲剧不管!他转身,
准备往对面楼跑,可刚走两步,又停住了。自己一个人去?万一真出事了,
一个人也处理不了。而且,深夜里敲别人家的门,万一真是误会,人家还以为他图谋不轨。
不如先去找点人,一起过去看看,也好有个见证。想到这里,他改变方向,
没有直接去对面楼,而是跑向了不远处的小卖部。那是这片居民区,
深夜唯一还可能有点人气的地方。小卖铺是厂里退休的老周开的,一间十来平方的小房子,
门口支着个简陋的15瓦灯泡,发出昏黄的光,在夜里像个小小的灯塔。
几个男人正围着一张方桌酣战麻将,打破了深夜的寂静。
老周则蜷缩在老式展柜后的竹制凉椅上,摇着一把蒲扇,
眯着眼睛看着柜台上那台小小的黑白电视机,电视里正在放《新白娘子传奇》,
白素贞正在和法海斗法,雪花点多得像漫天飞舞的棉絮,但老周看得津津有味,
时不时还跟着哼两句主题曲。王刚顾不便打扰,径直走到柜台旁的公用电话前。电话接通了,
王刚语速极快。“主任,我王刚…今晚的夜班,我……我可能要晚点到,或者请个假……对,
有点急事,我……我看到对面楼,七楼,好像……好像有人吊在阳台上了!
”他尽量压低声音,但吊在阳台上这几个字,还是像一颗冷水滴进了滚油锅,瞬间炸开了花。
麻将声戛然而止,所有打牌的人都停下了动作,手里的牌掉在桌上也顾不上捡,
齐刷刷地扭过头,惊疑不定地看着他。老周也猛地坐直了身体,脸上的肥肉颤了颤,
眼睛瞪得溜圆,手里的蒲扇啪嗒一声掉在了地上:“耶,刚娃子,你刚说啥子?哪个吊起了?
哪个楼?”王刚放下电话,转过身,面对着众人惊愕的目光,咽了口唾沫,喉咙发紧,
艰难地重复道:“我对面那栋,七楼,李建军他们家阳台……我刚刚出门看到,
好像……好像有个人吊在那里……我不确定,但看着太像了!”一瞬间的寂静之后,
是炸开锅的议论。“真的假的哦?莫乱说!建军和小兰两口子不是好好的吗?
”说话的是机修班的老吴,和李建军关系不错。“七楼?建军他们家?
我下午还看到小兰在坝子上晒被子呢!”“你看清楚没得?是不是衣服哦?夜里光线暗,
别是看错了!”“走走走,去看哈!看哈就晓得了!宁可信其有,不可信其无!”事关人命,
没人再顾得上麻将。老周第一个站起来,捡起蒲扇,顺手抓了柜台上的手电筒:“走!
去看看!”几个牌客也跟着起身,有的摸起桌上的烟,有的拿起自己的外套,
一行人七八个人,跟着王刚,急匆匆地返回了两栋楼之间的空坝子。而这个时候,
楼里一些还没有早睡的人,听到外面的动静,也纷纷打开门探出头来:“啷个回事?
大半夜的吵啥子?”“出啥子事了?”“好像是建军家出事了!”有人喊道。“走!去看看!
”两栋楼里面住的基本上都是纺织厂的职工和家属,抬头不见低头见,大多都认识。
而且本身这楼就传得邪门,一听说出事,更是让大家惊慌,没一会儿,一群人就来到楼下。
楼层结构有些特殊,每层四户,后来因为职工多,房子少,就改成了八户。
把原本的一室一厅隔成了两个单间,中间留了一条狭窄的通道。李建军家是右边靠里那间,
带一个小小的阳台,外面还有一户是只有单间的邻居,姓陈,大家都叫他老陈,
是厂里的退休工人,六十多岁,孤身一人,平时不爱说话,和邻居们来往不多。
由于楼道的灯是厂里统一管理的,晚上十点之后就自动熄灭,一群人吵吵嚷嚷,
像一股混乱的潮水,涌进了楼道,手电筒的光柱在黑暗中乱晃,
照亮脚下布满灰尘和杂物的台阶,以及墙壁上孩子们歪歪扭扭的涂鸦,在昏暗的光线下,
那些涂鸦显得有些诡异。脚步声在狭窄封闭的空间里回荡,王刚跟在人群中,心脏跳得厉害,
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,手心全是汗,紧紧攥着手电筒,指关节都泛白了。
他既希望是自己看错了,只是一场乌龙,又害怕真的面对一具冰冷的尸体。终于爬到了七楼,
气喘吁吁。砰砰砰!老周用力敲响了最外面的大门,声音在寂静的楼道里格外响亮,“老陈!
老陈!开门!出事了!”敲了好一阵,里面才传来一个睡意惺忪、带着不满的声音:“哪个?
深更半夜的,搞啥子名堂?还让不让人睡觉了!”门开了一条缝,
一个穿着灰色汗衫、头发蓬乱的中年男人探出头来正是老陈。他眯着眼睛,
看到门外黑压压一群人,手里还拿着手电筒,光柱照在他脸上,吓得他猛地后退一步,
睡意瞬间去了大半:“咋……咋回事?你们这是干啥?”“老陈,是我们!
”老周急促地解释道,“快,建军他们家可能出事了!我们看到阳台上吊着个人!
快开门让我们进去!”老陈愣了一下,眼神里满是疑惑,侧耳听了听隔壁李建军家的方向,
一片死寂,连呼吸声都听不到。他的脸色瞬间变了,嘴唇哆嗦了一下:“不……不会哦?
我刚才睡得沉,没听到啥子动静啊……”但看着众人凝重焦急的表情,他不敢怠慢,
连忙拉开门:“进来进来!快进来!”老陈打开了通道里的灯,那是一盏15瓦的白炽灯,
电线裸露在外,挂在天花板上,发出昏黄的光,昏暗得如同虚设,勉强能看清脚下的路。
房门虚掩着,没有关严,留着一条一指宽的缝,像是在邀请他们进去,又像是在无声地警告。
老周和老吴在前,对视了一眼,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恐惧。老周深吸一口气,伸出手,
谨慎地推开房门,吱嘎一声,门轴转动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刺耳像是鬼哭。
伴随着开门声,屋子里弥漫着的一股劣质烟味和剩饭菜的酸臭味混合在一起,扑面而来,
呛得人忍不住咳嗽。“建军?小兰?”老吴试探着喊了一声,没人回应。
所有人都顾不上客气,径直冲向阳台,阳台和卧室之间隔着一扇木门,也是虚掩着的。
老周一把推开木门,一股带着湿气的夜风扑面而来,吹得阳台上挂着的东西猛地晃动了一下。
两个胆子大的年轻男人,是厂里的搬运工,平时干力气活,胆子也大,
立刻拿着手电筒照了过去,两道光柱瞬间聚焦在那个悬挂的黑影上。
光圈首先落在那悬挂黑影的脚下,那里倒着一只木质方凳,凳面是长方形的,
四条腿有一条已经有些松动,此刻歪歪斜斜地躺在地上,凳面上还有一个浅浅的脚印。
光柱缓缓向上移动,照亮了那双穿着塑料凉鞋的脚,那双脚没有一点血色,
皮肤是一种毫无生气的青白色,脚趾蜷缩着像是冻僵了一样。再往上,
是深蓝色的卡其布裤子,裤脚卷起一点,露出脚踝,同样是青白色的皮肤。最后,
光柱颤抖着,定格在那张脸上。是张小兰!她的眼睛圆睁着,瞳孔散大,
空洞地望着漆黑的夜空,像是在看什么遥远的东西,又像是在盯着每一个闯进阳台的人。
舌头微微伸出,颜色发紫,嘴角挂着一丝黑色的血迹。脸色青紫肿胀,
早已没有了任何呼吸的迹象。一根小指粗细的麻绳,紧紧勒在她的脖子上,绳子的另一端,
系在阳台顶部那根粗陋的水泥横梁上。“死了……没气了……”一个上前探查的年轻男人,
伸手探了探张小兰的鼻息,又摸了摸她的颈动脉,然后猛地缩回手,回过头,
声音干涩而恐惧地对众人说道。尽管早有预感,但亲耳听到确认,
所有人还是感到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头顶,不少人下意识地后退一步,
有人甚至发出了压抑的啜泣声。王刚站在人群后面,只觉得一阵眩晕,胃里翻江倒海,
差点吐出来。他扶住旁边的墙壁,才勉强站稳,他真的看到了,那不是错觉!
一条鲜活的生命,就在刚才,以这种诡异的方式终结了。“快!报警!快去报警!